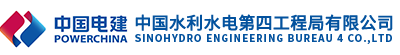書山有路勤為徑 |
|
|
|
|
世人常言書山險峻,唯勤勉可作梯;于我輩水電建設者,腳下卻另有一座山——是混凝土澆筑的巍峨,是圖紙疊壘的厚重,是需以工程人獨有的“勤”為徑,方能步步登頂的事業之山。 這“勤”,先見于手。 初到金塘沖項目,便撞見老師傅那雙手:粗糲如老樹皮,指節腫得像磨圓的卵石,卻能撫過剛拆模的混凝土面——那水泥尚帶著模架的余溫,掌紋蹭過毫米級的不平處,竟比讀書人指尖輕劃珍本典籍的字句更顯鄭重。青年技術員的手則終日握筆執圖,藍圖上的數據如星、線條如脈,密密麻麻都是他們日夜揣摩的“經文”。深夜工棚的燈盞下,計算器按鍵聲脆、鍵盤敲擊聲密,恰似案頭筆耕的沙沙聲,一邊演算大壩的鋼筋筋骨,一邊推演江河的奔涌走向。這手上的勤,是公式寫滿百張紙,是模板磨平千道棱,是把抽象的數字,一厘一毫釘成江河安瀾的基石。 這“勤”,更見于眼。 溢流面的每一根鋼筋,都要以目光為尺量——間距差半指、綁扎松半扣,都逃不過那雙眼;每一倉混凝土澆筑,都要以眼神為炬照——和易性偏了、傾落高度多了,即刻便要調整。目光所及處,毫厘皆不可失,恰似校勘鴻篇巨制的老學者,半字錯漏亦不許。高邊坡上更見這份專注:腰腹間的安全繩繃得筆直,像拴住峭壁的生命線,測量工程師半蹲在陡峭巖壁上,一手攥著巖縫里的灌木穩住身形,一手將棱鏡桿牢牢抵在錨桿根部——獵獵風卷著碎石屑打在臉上,桿身被吹得微微發顫,他卻盯著顯示屏上跳動的數字紋絲不動,連呼吸都放輕,只為捕捉支護結構那幾毫米的微小位移。這眼里的勤,是從萬千數據里揪出那點異常,是在龐雜工地里鎖死那處關鍵,更是在懸崖之上,把山體穩定的“安全密碼”一一破譯,將工程安全的使命,如錨桿深植巖層般,堅定不移“植入”每一道防護。 這“勤”,尤見于腳。 工程人的路,從來是踏出來的。從導流明渠的濁浪邊,到主體壩段的鋼架上;從砂石篩分系統的塵霧里,到拌和樓的轟鳴中——每日幾萬步丈量,踏遍工區每個角落,是建設者最尋常的日常。腳下或是雨后積泥裹鞋,走一步陷半寸;或是陡坡碎石硌腳,每一步都要攥緊扶手;或是鋼筋叢林的窄縫容足,得側著身子挪——可每一步都要踩實,每一步都得留心。這腳下的勤,是巡查時的“地毯式”走過,是驗證時的“點對點”抵達,是用雙腳去讀這本日日生長的“工程大書”,讀它的進度,也讀它的隱患。 可這工程之山的“勤徑”,從不是獨行路。它是老師傅把數十年經驗揉進言傳身教,如遞出一冊口傳心授的孤本,連掌紋里的訣竅都不藏;是年輕工程師攜簇新理論闖進場站,如執一把銳利刻刀,剖開傳統工藝的桎梏,讓老方法長出新筋骨。遇著難題,眾人圍坐如圍爐,似共解一道艱深習題——爭論聲激得茶水都涼了,演算紙堆得比安全帽還高,試驗做得手心起了繭,直等東方泛起曙光,才算把“答案”摳出來。這條勤徑,是無數雙手、無數雙眼、無數雙腳一起開拓的,是汗水滲進混凝土、智慧融進鋼筋里,一寸寸鋪就的。 終有,巍巍大壩攬住萬頃碧波時,條條銀線點亮千家燈火時,我們回望這座親手筑就的“書山”,當有頓悟:浩繁圖紙是我們的典籍,每一筆都寫著責任;精準測量是我們的訓詁,每一個坐標都注著嚴謹;雄壯壩體是我們的立論,每一方混凝土都撐著擔當。我們以勤為徑,攀的從不是虛無的學海崖,而是腳踏實地、能為萬民擋水送光的工程之巔。書山有路,這路上深深鐫刻的,是工程人用畢生之勤,寫就的無愧于天地、無愧于時代的壯闊篇章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